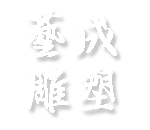公共艺术的评价最后 ,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如何衡量公共艺术的成功或失败。 Ch 1哥瑞斯沃尔德 (Charles Griswold) 对此曾有恰当的论述 , 可以引来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 “ ( 评价一件艺术品时) ,必须了解其象征系统 , 社会背景 , 以及它对观众的影响。”评价一件公共艺术作品 , 其复杂的程度 , 远甚于评判一幅绘画或其他自足类美术作品的价值。在评判一件自足类的美术作品时 , 我们主要关注其审美价值和市场价值 ,而在衡量一件公共艺术的成败时 , 于美学价值之外 , 我们还得考虑作品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含意。“效力 (Effectiveness) ” , 即作品所带来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同情心诸方面的显著变化 , 是判断公共艺术成功与否的一个有用标准。某些情况下 , 如果观众体验了一件公共艺术 , 在它的直接或间接鼓舞或推动之下而有所行动 , 则我们可以说这件公共艺术是 “有效力的 ”。不过 , 正如 S 1莱西 ( SuzanneLacy) 指出的那样 ,所谓 “效力 ” , 缺乏方法上的明晰性 ; 而方法上的明晰性 , 是在一个复杂而变动不居的世界里 , 为公共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和批判力提供准确的衡量尺度所必须的。比如 , 一个涉及众多人口的工程 , 是否就比一个只涉及一小群人的工程更有 “效力 ” ? 目的或行动 , 哪一个是中心呢 ? 或者 , 我们如何评价本身已成了公众的攻击目标的公共艺术 ?
公共艺术的开放性质 , 常常通过鼓励对心灵和社会进程的挑战而在民主社会中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 , 公共艺术展现并产生新的活力。从这个角度看 , 我们最好将公共艺术视为 “制造意义的互动过程 ”。它对新的、不断发展的阐释保持开放 ,藉此丰富自己每一天的生命。也许 , 成功和失败会成为一个暂时的判断 ,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 参与公共艺术工程的艺术家们需要明白 , 人们将以更广泛的社会标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检验 , 事实亦将证明 , 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永久。某些公共艺术肯定只是暂时的试验品 , 仅在有限的时期内有价值。
公共艺术亦可以作为衡量文明的一种尺度。有鉴于此 , 则公共艺术在宣示一国之成就方面的意义 , 甚至比国民生产总值或军队的规模更为重要。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文化 , 就像古埃及的金字塔 , 古希腊的神庙 , 或芝加哥、纽约的摩天大楼所证实的那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 公共艺术都决定于艺术家所构成的复杂网络 , 而艺术家又是在政治活动、经济发展等利益背景之中工作的。也许 , 最有生命的公共艺术 , 总是包含着人类的普遍关切。这些普遍关切突破了特定社区或民族的界限而向全人类说话 ; 它既引起特定公众的兴趣 , 又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游客的注意。这不就是古往今来的游人都急切地想去看重要的公共艺术的原因么 ? 不管它们在哪儿 , 也不管它们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
结 论
公共艺术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 也许比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军队的规模还要重要。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的传播中 , 公共艺术是一个关键因素 , 例如古埃及的金字塔 , 古希腊的神庙 , 以及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楼。考虑到公共艺术领域中的新发展 , 我们关于雕塑的初始定义 ( 在三维空间里 ,用固体材料再现人们所见的或想象的对象 ) 其前景如何呢 ? 可以看出 , 这个定义对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传统雕塑仍然有效。但是 , 我们必须修正这个定义 , 以便把公共艺术中近代和当代的新发展概括进来。比如 , 初看起来 , 社会雕塑似乎不是一种再现性的艺术形式 , 如传统所理解的那样。确实 , 社会雕塑既不模拟对象 , 也不复制对象。但是它可以在一种宽泛的意思上指向观念 , 只不过其主焦点已经从用固体材料做的雕塑转移到社会或政治的活动了。现在 , 社会雕塑既包含社会空间里的活动 , 也包含物理空间里的活动 ———不必一定是物理意义上的三维空间。在公共艺术中 , 时间纬度有特别的意义 , 因为时间既涉及历史 , 又涉及实时的思想和活动。
艺术家们仍在不断地创造出种种新的雕塑形式 , 包括光雕塑、土艺雕塑、装置艺术、视频、互联网及目前的计算机艺术等信息舞台 , 公共雕塑的传统疆界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拓展。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空间的出现 , 我们又得扩展我们的思维 ,思考公共艺术可能出现的不同形式。今天 , 公共艺术还包括瞬时的表演艺术 , 以及试图传递某种社会信息的 “行为 ”艺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例子 , 也许要数《媒体之灼 》 (Media Burn) ———“艺术和建筑协作组合 ”在 1975 年的一场表演艺术。在旧金山的牛宫运动场 (Cow Palace) , 蚂蚁农场 ?进行了一场公共艺术表演 ,其目的是批评大众媒体对信息的操控。在回应肯尼迪的一篇演讲时 , 一位艺术家扮演成肯尼迪总统 , 问聚拢的观众 , “你们有过用脚踹掉电视机的念头么 ? ”在人群的狂笑声和 《星条旗 》 ( 美国国歌 ) 音乐声中 , 两位勇敢的 “艺术家 - 宇航员 ” ( 艺术家扮演的宇航员 ) 开着一辆改装过的 1959 型卡迪拉克 , 以每小时 55 英里的速度 , 杵进一堵由 50 台燃烧着的电视机所组成的墙 ??猛烈的撞击把窜着火苗冒着烟的电视机抛到了空中。燃烧的电视机连续爆炸 , 人群爆发出阵阵狂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 当地的电视台把这事件作为当天的头条新闻做了忠实的报道。
哲学家们可能为了公共艺术的将来而去思索这些变化的含意。类似地 , 他们也可能为了美学而去反思发生在公共艺术领域里的诸多转化的含意。比如 , 有人也许要问 , 为了适应艺术的重建 , 把社会实践式的公共雕塑 , 以及技术上的创新 ( 如前面所引用的那些例子 ) 容纳进来 , 美学上需要做哪些改变 ? 也许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因为某些艺术实践 , 如音乐、戏剧、舞蹈一向需要协作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无论如何 , 激励艺术家和公众共同参与探索公共艺术的新前沿 , 有许多益处。通过扩展其益处 , 我们还可以为公共利益争取到许多空间。当然 , 创新性的冒险也总有被无知的公众势力扼杀的危险 ; 有他们的阻挠 , 便不可能产生重要的公共作品。解决这困境的唯一途径 , 是让社会公众参与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来而教育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