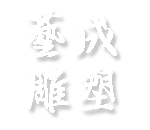一、 水意象
自洪荒时代起,“水”就进入了华夏先民的视野,通过漫长而深厚的心理积淀,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原始意象。在中国人看来,“水”与人相因相倚,富有性灵,充满情感。它浓缩了中国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多维多重的思考,昭示着中国人同化自然的理想情趣,折射了中国人的哲学、宗教、伦理、民俗、审美等观念,辉映出整个中华文化的特色。简言之,“水”意象契合了中国人道德与功业并重的认知,反映了柔韧而沉稳的民族精神,暗示了宇宙运行的生生不息。“水”的意象是我对写意雕塑在创作过程中永远不断回旋的母体。
老子几乎都是在围绕“水”阐发道理,而根据“水”意象创作老子,则是最好的选择。由是,《上善若水———老子》着重营构一种山涧缓流、氤氲浩渺的“水”韵,以此来喻示老子慧如涌泉的精神境界!作品中的老子寂坐不动,大千入怀,雍容高古,须发垂逸,似悠悠青云,在山之巅;全身的衣纹如依山而下的山泉瀑布,淋漓畅快、浮光跃金,闪烁其间;物在恍惚中,象在恍惚中,似与不似,意合无垠,一种如“水”般不粘不脱的神韵跃然眼前。可见,我们所想象的古人一定的文化意象中的古人,而不是现实当中的;经过历代人的想象,已经把最美好的想象投射在古人身上,他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已经与他的思想和时代融为一体,在我们的世界中已经失去了作为个体而存在,所以,老子就是一种意象。
二、 复合意象和意象群
中国文化中的“水”意象,还具有很强的生发力和粘合力,它与另一些常见意象结合,构成百态千姿的复合意象和意象群,产生了难以尽言的审美和文化效应。比如,《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对比“水”与“山”的不同特质,认为仁者所具备的宽厚仁慈、博大无私等品格,恰似“山”的宁静稳固与长久。所以,“山”“水”结合,成为反映儒家思想的重要意象。再如,禅宗艺术格外青睐“云”意象,借其象征随缘任运、无心自在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境界。在唐代禅僧寒山的山居诗中,随处可见“云”的悠闲自在:“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白云高岫闲,青嶂孤猿啸。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自在白云闲,从来非买山。”
孔子的概念,早已超越了“古人”孔子,而化为一座超越时空且巍然屹立的文化泰山。孔子的造型,在人的生理结构与山体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远观,自上而下纵观,山脚、山腰、山顶,层层递进;自左而右横看,道道天沟,一泻而下,纵横万里。或峭壁奇凸、或峰壑互生。近看,孔子面含春风,仁慈之意从脸上道道皱纹中绽出,似山脉水系,流韵弥长。智者仁相,浑朴凝重。这种文化与自然的双重意象使得它与现代都市环境虚实共存,古今相融。
在昙曜意象的形成过程中,我将人物的种族特征和生理结构中植入大量对当地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交集感受:袈裟飘忽,逸气袭人,广袖似云,衣纹若水,身体似绝壁、似悬崖,奇峰凸兀,独立苍茫,自成山水奇景自有佛意荡漾,暗合郦道元《水经注》中对云冈石窟地区大环境的描述。
在这里,《昙曜像》成了天地间的云冈,通体的山水意象塑造,隐喻着云冈的风水云气。而他的超然风骨,则成了云冈自然环境的必然,见证着这位高僧在历史空间、在佛教圣地的价值存在。
三、 现代写意雕塑与诗歌
现代写意雕塑与其他艺术类型也有很多的借鉴与交融。比如,现代雕塑与书法,与中国传统绘画,与诗歌,与音乐,与原始雕塑、中国传统雕塑等,它们不仅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而且还相互借鉴。下面主要说一下现代写意雕塑与诗歌的借鉴与交融。
现代写意雕塑超越了媒介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审美法则,恰恰要通过视觉形象来表现诗歌的本质。如果仿照苏轼的说法,就是要实现“诗塑一律”、“塑中有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第一,两者皆强调“神”、“理”、“象外”,不重形器,突出意象创造。第二,两者都是为了寄兴怡情,抒发意志。第三,两者均注重意境营造,传达深邃的宇宙情怀和郁勃的生命精神。
现代写意雕塑高标模糊的造型手法,就是为了尽可能摆脱现实形貌的束缚,让作品具有更多的回味空间。《言子》中,我有意将老人的衣纹刻得很深,远远超出现实衣纹的视觉效果,使之剥离观者的习惯性认知而趋于独立,从而进一步引发观者的联想,生成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这不仅是衣纹,更是伤痕,是刻在肉体上、精神中、民族记忆里的伤痕,让人触目惊心,无法忘记。
现代写意雕塑讲究肌理的独立审美价值,综合运用各种技法使表面呈现丰富的视觉效果,以此留住观者的目光在作品中绸缪盘桓,从观照方式上强化时间性特征,也让审美过程更富诗性意味。
此外,现代写意雕塑青睐的凝练、简约、跳跃等审美风格,亦与中国传统诗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标准相通。诚如杜甫所言:“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一是,创造兴象。“兴象”的关键在于“兴”。何为“兴”?首先,“兴”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发端引起歌咏内容。简言之,就是假物取义。从形象生成的角度看,“兴”(即主观情思)与“象”(即客观景物)之间的契合交融,是当下即成且浑然无迹。
现代写意雕塑创造“意象”的手法,正是“兴象”的生成方式。一方面,作者穿越形象信息的直接性和表面性,假物取义;另一方面,创作者将油然生出的情感冲动表达出来和外物实现契合,达到超越主客,与物同化。
《上善若水———老子》和《老子出关》,同样的对象,一个起兴于水,一个起兴于枯木,前者围绕水的意象进行创作;后者造型枯瘦干硬犹如一段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似与不似之魂———齐白石》起兴于齐白石笔下的一幅画:一块巨石上蹲着一只小鸟。鸟与石的关系,便成为该作品中头与躯干的关系,其中的大小对比、粗细对比,生动再现了齐白石艺术的美学精神。
二是,朦胧诗性。现代写意雕塑还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追求朦胧诗的意境。但朦胧诗与古典叙事诗、抒情诗不同,它完全扬弃了写实,不再恪守首尾贯通的逻辑因果链条,不再单向固定平面叙述,而是以意象的大跨度组接打破物理时空秩序,打破线性认知结构,重筑瞬间感受的心理空间。朦胧诗还注重意象的立体组合,表达的意象也更加含蓄、凝练且富于跳跃性。朦胧诗尤其突出哲学意识的全方位渗透,作品的空间意指大大拓宽。
《扎辫子的小女孩》、《三乐神》、《依依情深——母与子》等作品,意境都近似朦胧诗。这些作品由不同材料综合构成,犹如蒙太奇意象组合结构,造型离现实更加遥远也更富精神性,给观者腾出了更多的心理空间。尤其《扎辫子的小女孩》,雕塑的两条腿用两根木棍直接表现,与脸部躯干等意象并置时形成视觉感知的大幅度跳跃——从真实性的形象忽然转到了象征性的视觉符号———显然,这种跳跃性带来的审美空白,更能激发观者通过想象力来填补,从而强化了作品的直观性和流动感,创造出更为自由的精神空间。
《唱支山歌》、《春风》等作品,某种程度上也与朦胧诗有相通之处,即:意象若隐若现的较低辨识度,酿出漂泊不定的想象空间,进而拓展了作品的意指范畴,正所谓“妙在含蓄无垠,思考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叶燮《原诗·内篇》)而且,这些作品的意识表达和情感诉说更为抽象,也更为复杂,呈现的精神本质则更为直接。